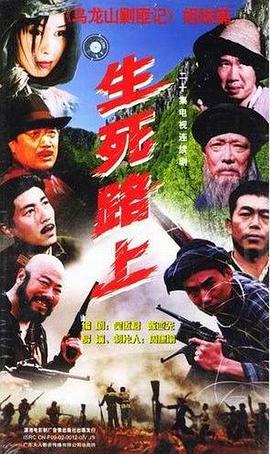更新:2025-07-05 12:20
首映:1949-09-13(日本)
年代:1949
時長:108分鐘
語言:日語
評分:8.7
觀看數:73861
熱播指數:7171
來源網:三年片免費
晚春:不要溫柔地走進這新時代
即使在很多歐美名導的電影里,也有對小津致敬的段落,很主觀的,我覺得沒有一個成熟的中年人可以拒絕小津影片流露的安靜和雋永。生活如此瑣碎如此無奈如此脫離軌道,可還是有一些希望,有時是一股很淡很淡的溫情,有時是散漫出來巨大的失落,有時是生命不可抗拒的流逝,讓觀者只能吐出一句,that’s life. 轉回旁觀者的心態和視角,扮演一回生活的過路人,抽離一下,逃避一下,輕松一秒。小津的鏡頭空靈自然,讓人容易忽略,從而走進了人物的思緒。導演若不是細膩敏感人性到相當程度,如何能拍出來?很自然的

探討人一生都在被約定俗成的規矩所束縛著,絲毫沒有喘息的機會,尤其是那個特定時代下的女性,只能淪為男性的附屬品,丈夫在喪偶之后可以再婚,可女性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。
最可怕的是,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別人,絲毫沒有顧及人的主體意識,片中每個人婚姻觀都不相同,但是都認為到了這個年紀應該結婚,這已經變成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,當紀子被迫答應時,所有人都歡天喜地,因為這滿足了自己的價值需要,而且還要問“這是你自愿的吧,沒有收到逼迫吧”,將自己心中最后一點愧疚感也擇的干干凈凈。

“小津是電影界對日常生活最敏銳的探索者之一”。“與溝口不同之處在于在掌握了西方的電影手法之后,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區別于任何體系敘事系統,突出了日本民族所特有的社會心理和審美觀念”,兩次看小津的電影,都會流淚。《東京物語》是在母親去世前的那一段,《晚春》是在紀子穿上婚紗在家中等待出嫁的那一段。觸動我的是生活中的那些平常、瑣碎,那些不得不妥協的無奈和溫暖而偶爾詼諧的溫情。“日本人強調佛教禪宗思想中的靜形和定神,把它作為民族的精神核心,符合了日本人的心理和審美要求”,安靜和平和

小津安二郎的拍攝手法對女性角色的處理
攝影師的觀看方法
藝術批評家John Berge在《觀看之道》中提到:「攝影師的觀看方法,反映他對題材的選擇。」「我們對影像的理解和欣賞還取決於各人獨具的觀看方法。」(Berger, 1972: 3)影象的觀看方法,表達了觀看者的態度。所有藝術形象,可以說都是根源於客觀物象的,然而在與客觀物象的具體聯繫方面,又往往呈現出很顯著的差別。同樣地,同一拍攝對象落在不同導演手上,亦會得到完全不同的表現。
導演最為人津津樂道的,是他在攝影機位置導致的鏡頭角度,小津安二郎多以低視點攝影方法,把鏡頭在離地面兩至三尺的低位置,避開一切俯瞰的鏡頭,他曾經說過:「不應該濫用俯瞰攝影來表現人。」(佐藤, 1981: 212)這是因為抬起頭看人具有尊敬人的謙虛。而他在影機運動的禁絕,避免了在鏡頭上造出對角色的偏頗,加入了個人情感。可見小津以一種人文主義精神,去形塑出每一位主角。
晚春對女性的塑造
黃國兆在《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世界》中提到,小津對家庭倫理電影的情有獨鍾,在他大部份的影片

如果帶著現在很多人看電影的心態去欣賞小津安二郎的電影,大約是會失望的,因為他的電影里表面上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,沒有激情場面,沒有炫技的鏡頭,沒有搞笑的臺詞。然而,我卻一直喜歡有嚼頭、留余味、讓人思索、給人啟示的故事,因此,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非常符合我的喜好。他電影里出現的風聲、雨聲、音樂、人們說話的聲音,光線的變動,房間里的設置,旅館、餐館,風景,服飾,日本傳統劇目等等都是有意味的,讓人深思。
一開始以為《晚春》是一部簡單的述說父女之間情感的電影,看完了發現它遠遠不止如此。雖然我無法欣賞電影里曾宮教授與紀子看的日本經典傳統劇目——能劇,但其中唱的那句“······連樹木和花都被教化······”,卻久久揮之不去。
是的,一切都被教化,人被教化,人教化了一切。紀子完全不知道舅舅與其再婚妻子的相處,卻表示出完全無法接受和理解舅舅的再娶,覺得是丑惡、骯臟、不體面的事情;即使曾宮教授的學生服部與紀子相互了解,在一起游玩時是那么輕松、自由和愉快
退休教授在家寫書,二十七歲的女兒一直照顧父親,無微不至。在別人的提醒下,父親終于意識到女兒該出嫁了。女兒不愿意結婚,發脾氣鬧別扭,擔心父親的生活,最后是父親說我會開始新生活,女兒才高高興興的出嫁。
都是日常生活,開始父親回到家衣服都是隨手一脫地上一扔,洗個臉都要喊女兒遞毛巾,喝茶喝酒吃飯刷牙都要人伺候,最后一個場景,父親自己回到家,脫下西裝自己掛好,拿起桌上的水果開始削皮,皮斷了,父親陷入了思索,沒有人陪伴照顧的生活確實不一樣了啊。
沒嫁人之前怕嫁不出去

晚春:不要溫柔地走進這新時代
轉載請注明網址: http://www.3wbaidu.net/zhonghe/vod-35491.html